蒙城汇
标题: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6) [打印本页]
作者: 此时此刻 时间: 2016-6-25 20:43
标题: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6)
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16)
文:林炎平
华夏的道德历史——寻求青天大人
于是,作为剧种,华夏只有“怨剧”而没有“悲剧”,华夏的“怨剧”是在祈求上苍的同情和“青天大人”的明察,而古希腊的“悲剧”是在激起蕴藏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力量和对于正义勇敢的共鸣。国人并非没有愤怒和抗争,悠久的孟姜女的故事,也许就是这种情绪的最终表达,但却显得很无奈很悲惨。孟姜女的哭诉,并非要唤起对于人的价值的认识和抗争的勇气,而是在寻找一个终极的听众,亦即一个超自然的“上苍”或人间的“青天大人”。
正由于没有“悲剧”,华夏也就没有了“喜剧”,而只有“闹剧”。在那没有多少幽默感的傻笑之中,到底有多少真理的启迪和道义的力量?实难恭维。每年闹腾的“春晚”,也许是中国既没有“悲剧”,也没有“喜剧”的最好的诠释。留下的只有“怨剧”和“闹剧”了。当然,还有华夏色彩独具的剧种——“颂剧”,这也许应该归在“闹剧”之中。
华夏百姓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祈祷和祈求的是一个可以解救他们的“救星”和“青天大人”。中国的道德历史,就是一部哭哭啼啼闹闹腾腾的寻求“青天大人”的演义。国人需要一个“救星”,由他来掌握百姓的命运,而百姓只需俯首听命、歌功颂德。“济世自有飞天剑,尔且安心做奴才”。数千年来在“皇恩浩荡”之中,不少国人已经没有了对人的价值理念。他们在被损害时的逆来顺受和他们有朝一日得势后的飞扬跋扈,源自同一个心理和价值观:个人价值是不值得尊重的。他们在底层时的逆来顺受是将这一理念用于自己的体现,他们在得势后的飞扬跋扈则是将这一理念用于他人的结果。
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个人主义”者,而最终都必然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即“恶狼主义”者。只要有机会,他们可以用任何别人的福祉换取他们的私利,他们可以对于别人的痛苦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悲惨处境熟视无睹,他们可以把别人看作仅仅是他们向上爬的台阶和垫脚石,他们可以在谈论别人的生命时根本不觉得这是和他们有同样权利的同类,而是一些可以利用的筹码和数字。这就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的恶果。
华夏自古以来并非没有仁人志士,华夏最高境界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应该体现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字里行间体现着责任和牺牲精神,每个现代的国人都应该为此而感动和惭愧。范仲淹不仅仅抒发了他自己的志向和情怀,也没有忘记他的人民和皇帝。他个人的心情和感受,随着自然界的伟力而跌宕起伏,但是坚如磐石的是他的信念。
我十分喜欢范仲淹的这篇散文,不管在穷愁潦倒还是春风得意时,总不禁会背诵这篇散文。或喜或忧,人生任何时候都处在这两者之一或者之间。能够做到无论何时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绝非易事!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其距离以人为本的理念还相当遥远。就是如同可以写出《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这样的不凡人物,仍然在随时矫正自己以符合他上司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把原则和理念置于权势之上。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人生困顿时,李白的诗句无疑振奋人心,催人上进。但是甚至像李白这样不拘一格的人,都不能幸免对于个人价值的误解。“行路难”中念念不忘:“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绝非趋炎附势之徒,他可以蔑视权势,但是当他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却不得不把得到皇上的赏识作为他抱负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也不能脱离对于权势的依附,似乎这是唯一可以实现抱负的途径。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而如此经年累月的对于权势的屈服和依附最终让英雄也气短。
于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鲁迅)于是,华夏少有真正的英雄。那些被中国后人奉为“英雄”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积聚了过去和现存的污泥浊汤并以此兴风作浪让其荡涤社会的人,他们不仅没有带来人格的进步和社会的公正,却致力于利用人性本来的丑恶和消灭社会仅存的良知。
西方对于个人价值的重视并不仅仅体现在那些史诗般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同样,对于西方来说,这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积淀。一些看来不大的事情,却体现了一个社会和民族的价值观。一场大灾难中的小事情令人回味。
我远道去上海见一个瑞典的客户,适逢地震袭来。西方人似乎尤其珍惜生命,为了躲避从远隔千山万水传来余震,瑞典经理让所有员工在街心公园休息,进而把大家都放假回家,但是不好意思让远道而来的我们打道回府,居然她自己和我们回到她认为有危险的大楼去洽谈。我看得出,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对地震很恐惧。会谈后,我感谢她冒着危险和我们面谈。我知道,她是冒着她确信的危险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否则她不会打发所有的员工早早回家。
那次地震震中的惨烈我到了当天晚上才知道。瑞典办事处经理对此事的处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公司没有和其做成生意,但是此事却让我钦佩这位经理的行为。她显然是把雇员的安全放在了经济利益之上,而且她还把自己的安全放在了雇员之下。我不得不说,在西方普遍弘扬的“个人主义”中,包含着对于其他个人和所有个人价值的尊重。以致在不经意间,那些普普通通的西方人就流露出他们的理念,并且付诸于行动。
和这个事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作协委员的一首无耻诗词。其是中国式“集体主义”的最残酷和本质的写照,这样的无耻在任何崇尚人的价值的地方都不可能看到。这首词并不出于压力和逼迫,而是作者内心积淀在这不寻常关头的真实流露,他是真正地感到了召唤,从而倾泻出了此等肉麻和无耻。如此自觉地对于他人生命和价值的蔑视和践踏,需要长期的心理折磨和道德降解。
在他看来,这么多死亡的个人,是无法和一个抽象的“集体”和权势相比的。人的价值不过是可以任意牺牲的数字或者符号。但是这样的人,对于自己的利益绝不这样看。他唱的高调都是让别人去相信和实践的,他自己绝对不愿意就这样“亲历死也足”,更不愿意在坟墓里看奥运。他是要这些死去的人不要给活着的人带来愤怒,不要给他带来内心的责难,他要让那些死者的亲属认为“做鬼也幸福”,既然死者很幸福,那么幸存的也就更满意了。于是让他可以安安心心舒舒服服过日子。
个人服从集体,而集体则由某些少数的利益集团所代表,从而所有的个人服从某些个人,这样的形式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集体主义。无论以什么样的慷慨激昂和群众运动做幌子,都无法掩饰其真正的本质。
宣扬“集体主义”导致的个人崇拜和极端自私
我们稍稍回首,便依稀可见那个还未远去的荒唐时代。对人格的集体侮辱莫过于那时的“忠字舞”。那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集体行为,舞蹈大致如此:用手在胸前一笔划,算作是一颗红心,然后把手伸向空中,意思大概是把心献了出来。通篇都是这样的舞蹈语汇,整个民族作为一个集体,每天整齐划一地跳舞,表达一个集体对于某个个人的忠心。这个全民参与的集体舞,跳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终极诠释了中国式的“集体主义”。
忠字舞的荒唐似乎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忠字舞的基础却根深蒂固,主子阴魂不散,奴才忠心仍在,卷土重来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
在集体的名义下,所有的人都被要求为某一个“代表集体”的极少数牺牲自我。一些人的权力欲急剧膨胀,更多人的权利随之消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褒扬集体主义的民族,却源远流长的是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
难道集体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及个人崇拜是如此相辅相承吗?结论是肯定的。中国式“集体主义”的本质,在于消灭普适的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内心的道义准则和独立的人格。随之而来的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极端卑躬屈膝自私自利和个别人的飞扬跋扈专制独裁。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一针见血地批判此类集体主义:“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他显然指的是为了否定个人价值而推崇的“集体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私有制”的否定不能带来对于“公有制”的肯定,实际上过去搞的“公有制”最后都无可救药地变成了“公无制”,人人一贫如洗,只有极少权贵拥有一切。从消灭“私有制”开始,以“公无制”的结局告终,这是必然的。这就如同你否定了每一滴水的价值,肯定不会再有江河湖海,很可能最后连一口小水塘都是臭气熏天的。
曾经在华夏盛行的“集体主义”,仅仅是为了消灭普适的个人价值而已,于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人价值丧失殆尽,却导致了极少数人的个人价值无限放大。所以,在中国式“集体主义”最盛行的时候,也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利益最蔑视的时候。
我的华山之行使我产生对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彻底怀疑。1976年10月初,是中国值得铭记之巨变的开始。当时我对于前途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愚公那个蠢驴也许无法让我这一辈子再次把太行山搬一遍了。我别出心裁决心到华山去一趟。那时还没有旅游这么一说,一个人去华山是需要一定疯狂才可以成行的。村里没有分红,只好靠逃票成行。
当时的华山,是非常值得去的。一是它挺拔苍凉的自然景观,二是它劫后余生的人文景观。 “自古华山一条路”,当时几无人迹,越发彰显华山的内涵和个性。即便不看华山的任何人文影响,它的自然景色也可谓鬼斧神工,引人入胜。刀劈似的峭壁,直上直下,整座山峰就是一整块巨石,这是黄山和别的山无法比拟的。如果说黄山是秀美,那么华山就是壮美,华山让人联想到男子汉裸露的胸膛。但是那人文的痕迹使人非常感慨。这是一个被当时的“忠字舞”的“狂舞者”们刻意破坏后彻底忘记,被当时的歌舞升平完全遗弃,又尚未被此后的铜臭所污染的人文废墟和自然奇观。
山上所有古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连狭窄的石头小径边的历经数个朝代安装的护栏都被“忠字舞”小将们掀到山底去了,仅留下一些残柱。我曾经听说过“第二次解放华山”,后来知道这就是指“红卫兵”到华山上把那些“四旧”都砸烂。当时的我是自身不保,食不果腹,衣仅蔽体,那天上华山也如此,我只带了朋友送的半斤饼干,这是两天的全部食品。除了身上穿的球衣裤,没有别的衣服。尽管如此,我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这种看来和我无关的破坏的反感。
那是一个月圆的日子,晚上在苍龙岭附近道士破旧的观里歇了几个小时,早上四点,乘着月色就去东峰看日出。在接近东峰的时候,看到另外几个上山的人,大概那天上山的一共也就这么几个人。十月的华山清晨很冷,太阳出来还要一些时候,于是就在这距离东峰不远的旧庙里歇一会儿。很快,那几个人就说太冷,要找东西生火取暖。山上的灌木他们是弄不来的,结果,他们居然想到了把空图四壁的旧庙的椽子弄下来做燃料。我对他们说,并不很冷,不要弄坏旧庙。我当时比那几个人穿得还少,如果我不觉得太冷,他们也一定不会太冷。但是他们执意要把椽子弄下来,把一根绳子抛上去,拉住椽子,用力向下拉。我当时没有更好的制止他们的办法,只觉得这事情简直太损了。他们要我帮忙,我拒绝了。好在这几个人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折腾了好一会也没有什么成效,只好气喘吁吁作罢了。估计他们经过这运动也不觉得冷了。
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不忘。我对自己不能制止他们感到很惭愧,对他们的这种行径倍感愤怒。就为了一点点自己眼前的利益便胆敢破坏属于整个民族的文物,如此的贪婪和愚蠢,令人绝难原谅。看到这样一幕,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华山上的古迹都被破坏了。可以撼动的,都被“忠字舞”小将从山头推下了山沟,连栏杆云梯也不能幸免。当时华山的石径已经几乎没有扶手和栏杆,只有那些从巨石上凿出来的无法撼动的石头台阶还安然无恙。
我很难理解是什么使得这些本来涉世不深的学生热衷这么残酷的破坏。这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遍及华夏大地和整个民族的普遍行为。全体附庸极少数的权势,丧失个人理智而导致集体疯狂,把属于整个民族、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古迹破坏贻尽,这是“集体主义”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的培养使得他们对他人极其蔑视,对他们不理解的事物极不容忍,对于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极端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他们理解的“集体主义”和“正义”,于是有了我永远挥之不去的华山一幕。
当我登上华山东峰时,太阳还未出来,月亮尚未隐去,东方已经发白,在寒冷中祈盼日出是一种幸福,因为这一刻肯定会到来,因此等待不会没有意义。在喷薄而出的华山红日照到我这个饥肠辘辘、衣不御寒的太行山知青身上时,我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身份。我似乎同时感觉到了自己对于天地的渺小和重要,使得渺小的自己感到重要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这也许就是我后来意识到的被西方推崇的“个人主义”。这使得我对于当时完全未知的社会变革更加有信心,更加希望我可以参与其中。我当时并不知道古希腊和西方的思想,自然不理解人的价值。但是我在那一刻所感觉的,却在日后的人生经历中被反复品味,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那天正是阴历闰八月十五,那年有两个八月,于是有两个八月十五,每个我都记忆犹新。数年后,我在大学里写下这样的诗句时,最初的酝酿必定是当年华山的景象和经历。
七律·中秋
今夜明月今夜酒,
西风时节宴中秋。
身无分文忧天下,
心有余力费躇踌。
飘零已谙人生苦,
浮沉渐泯世间愁。
阴晴圆缺四海共,
何必相逢叹如勾?
为“个人主义”正名
我相信,任何民族的个体都在本质上存在着朴素的对于自身价值和他人价值的尊重。“人之初,性本善”,想必是有道理的。因此,这种价值的被弘扬或者被扼杀是由于环境,而不是遗传。如果一个社会环境惩罚善良和独立的人格,而奖励丑恶和奴性的人格,那么久而久之,只有丑恶和奴性的人格才会以适者生存的法则胜出,成为这个社会的普遍人格特点。而这种人格特点又反过来进一步恶化社会环境。这是一个正反馈系统,亦即社会环境导致了人格的恶化,人格的恶化进一步导致社会环境的恶化,再进一步导致人格的恶化。正反馈系统的结局只有两种:在没有强有力约束的情况下以系统崩溃而告终,在有强有力约束的情况下形成不收敛的振荡。在华夏发生的显然是后者,千百年来不乏朝代更迭,不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却不见人格的进步。
国人现在的自私,至少一部分来自于千百年来的对于“个人”的压抑和对于“集体”的弘扬,所谓“集体”并非社会大众,而是让个人牺牲自己的价值和出卖自己的良心以便和权势保持一致。这样的世世代代对于自私的培育,自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在中国,少有人会把公用电线剪断、马路的窨井偷走当废品卖钱的。这很难说和虚伪的所谓“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长久说教没有关系。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极端自私自利的行为和社会风气就是这些虚伪的说教和相反的现实所共同培育的。
和中国的冠冕堂皇的“大公无私”不同,在西方,人们对于自己的照顾是理直气壮的。如果在国外乘坐过飞机的话,就一定会在安全指示中听到这样一句话:“如果碰到舱内失压,氧气面罩会自动弹出。此时,请立即戴好氧气面罩。如果有人需要帮助,请务必在自己戴好后再给予别人帮助……。”现在中国的飞机上也如此要求乘客。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每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使得自己不成为别人的负担,同时,尽可能去帮助别人。
由于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是天经地义的,西方人在竞选政府官员时,都强调自己注重家人和家庭,在竞选场合经常带配偶和子女出席,以体现竞选者对于自己家庭的重视。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文革”时代,虚伪的“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说教还促使了一些人装模作样的表演,他们到处声称自己的不重要、家庭的无所谓,甚至在那几部绝无仅有的戏剧和电影中见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以此表现这些人的大公无私 —— 既不顾自己,也不顾家人,在他们心中只有人民大众。但真实的现实却恰恰相反。他们积虑“谁主沉浮”,要超过“秦皇汉武”,为一己私利不惜涂炭生灵,为平步青云不惜落井下石,他们永远不会是“个人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别的个人;他们也绝对不会是“集体主义”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集体只是一个试验的对象和攀登权势高峰的阶梯。
中国式的“集体主义”并不在于重视集体,而在于无视个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宣扬“集体主义”的真正目的并非弘扬和肯定集体,而在于蔑视和否定每一个个人。那个“集体”是如此地虚无缥缈,它既不是个人的集合,也不为由个人组成的集体服务,它只是一个被权势者创造出来否定“个人”的冠冕堂皇的抽象概念。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就是集体的化身。
正因如此,多年的“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说教,造就的却是极其自私和虚伪的群体。在中国,没有集体主义也没有个人主义,有的只是对于他人价值的极端蔑视和极度膨胀的利己主义。如果任其发展,必如愚公把他的愚蠢和贪婪代代相传,其危害真的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和中国式“集体主义”截然相反的,是古希腊要讴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古希腊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在意自己的清贫生活,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毫无实际功利可言的理想,才使得后人有可能成就现代文明。我深深敬佩古希腊哲人和学者,那时的学术研究,既没有什么高额的工资,也没有什么光荣的奖项,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功利,因此,他们持续一生的高尚行为,只能源于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探索真理的个人勇气和寻求社会公正的利他精神。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标签都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个人主义的典范,也是集体主义的榜样。
个人价值得到尊重的社会,才会产生这样的英雄。尽管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也比比皆是。那些甘于清贫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些握有权力但是倡导民主的政治家,如索伦和伯里克利;那些为了全希腊利益而战死疆场的无名将士,都是在这样的理念和制度下才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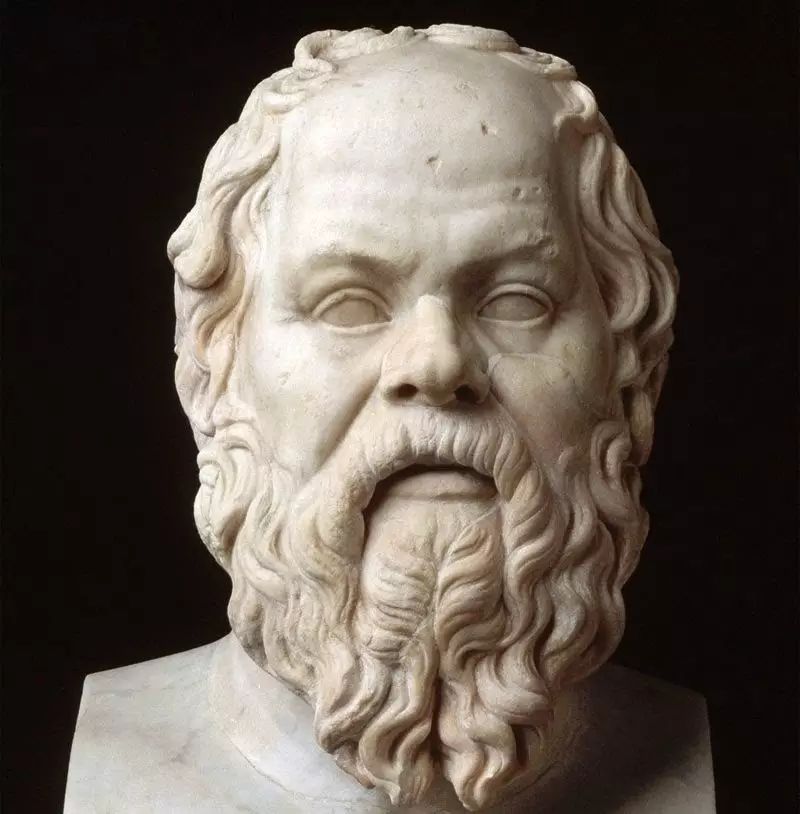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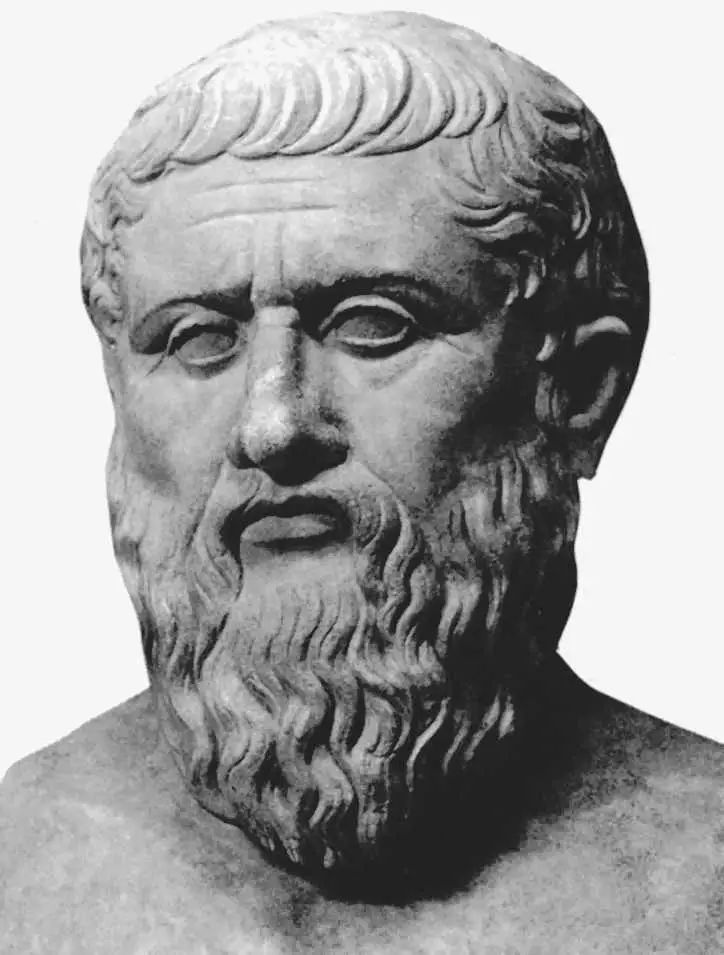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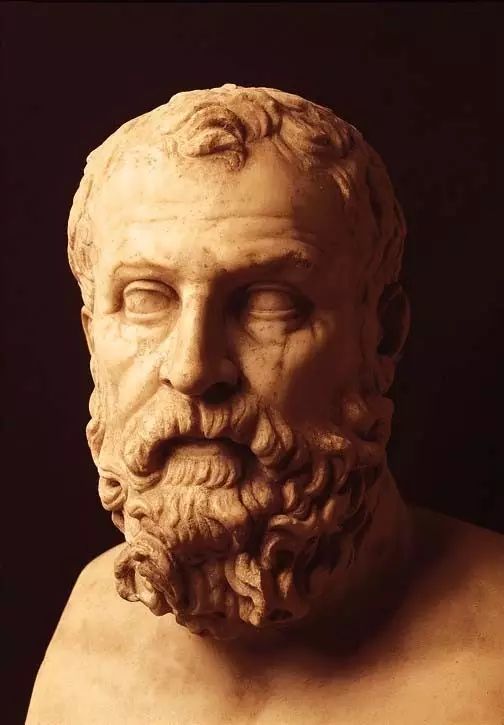
古希腊政治家索伦
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
西方正是通过文艺复兴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才会在此后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科学、艺术和政治的英雄。他们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典范,也是重视整体利益的榜样。
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诞生的理由,而更是对其每个公民价值不容置疑的誓词,“每个人生来平等,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如雷贯耳的词句,蕴含着正义,激荡着风雷。正是对于每个个人价值的肯定,遂使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也为了整个社会和他人做出了贡献。
蔚蓝的澎湃必来自无数清澈的涓涓细流,污泥浊汤也必源于众多的腐败肮脏。社会的进步始于每个人的内心,如果我们还怀有对他人的善念,对自我的尊重,那么,是从自己做起的时候了。
中国不需要“愚公”,而急需“普罗米修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普罗米修斯,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赞美他的精神。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法】尼古拉·塞巴斯蒂安·亚当作品
美好和正义,是从赞美她们开始的。
| 欢迎光临 蒙城汇 (https://mengchenghui.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4 |